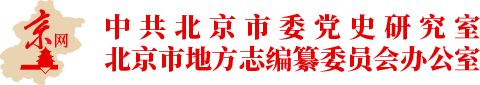红楼学人里面学问精深、性格鲜明者比比皆是,要论最“痴”最“狂”的,不能不提到黄侃。他骂过专制腐朽的清廷,也骂过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他治学精深又固执保守,尊师重道又倨傲不羁。他不拘小节、特立独行、恃才傲物……终其一生,留下一代国学名士的许多趣闻轶事。

黄侃
痴迷国学
黄侃,1886年生于四川成都浙江会馆。父亲黄云鹄为清朝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特别重视对他的教育。黄侃幼年聪慧过人,熟读四书五经,人称“神童”,16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因父亲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交往,他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不久,黄侃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结识章太炎并跟随他学习数年。回国后,他奔走各地组织反清活动。
1911年7月,黄侃针对清廷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奋笔疾书,为武汉《大江报》撰写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鼓动新军造反。此文见报后,风行全国。清廷震动,查封《大江报》,黄侃侥幸脱险。后来,他目睹民国政治腐败,逐渐转向学术研究。1914年秋,黄侃应北大邀请,受聘担任国文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辞章学、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黄侃治学勤奋严谨、孜孜不倦,已达痴迷程度。他为节省时间做研究,将馒头、辣椒等放在书桌上,饿了就用馒头蘸辣椒往嘴里送。一次看书入了迷,他误将馒头伸进砚台和朱砂里,结果把自己涂个大花脸却浑然不知。正遇朋友来访,见他如此模样,便大笑起来。黄侃竟一脸愕然,不知朋友为何而笑。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领域有很深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是学问精深。所治经、史、子、集诸书皆能应答如流,具体到某篇文章,甚至某页、某行,令人惊奇。他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还常教育学生,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他讲授《文选》《文心雕龙》等课,生动传神,尤其是抑扬顿挫的朗诵,吸引许多其他系的学生前来听课。课后学生们纷纷模仿他的音调,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时听课的学生、后成为国学大师的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
黄侃曾说:“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该圈点书籍五部。”他如是说亦如是做。黄侃在课堂上讲授《说文解字》,不带原书,不带讲稿,却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学生们下课以后去查原书,发现讲解一字不漏,一字不错,都佩服得不得了。课堂下,他的《说文解字》每一页里面,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色笔记,有朱笔批红,还标有各种各样的符号。《说文解字》全书解读了近万字,每个字后面都录有前人的讲法,也有他的理解。对各家之说,他有的肯定,有的否定,逐条记在上面,可见钻研之深。
新文学的反对派
当时北大汇集学界新旧各派翘楚,堪称学术重镇,在此任教的既有辜鸿铭、林纾、黄侃等保守派,也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等新派人物。黄侃以名士自居,以求学问育人才为己任,为人刚直,我行我素。
陈独秀受聘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校长蔡元培召集文科教职工欢迎他。众教授碍于校长面子,还算客气。突然,黄侃头戴黑色短㏾瓜皮夹帽破门而入。因陈独秀大力倡导文学革命,两人关系素来不睦,黄侃一看是他,大笑一声叫道:“一个区区桐城秀才,也值得这么兴师动众么?”话音未落,即转身狂笑而去,令陈独秀尴尬不已。
即使对自己的同门,黄侃也同样不讲情面。黄侃与钱玄同同为章太炎门生,黄侃以大师兄自称,戏称钱玄同为“钱二”。二人在北京章太炎寓所相遇,因不满钱玄同等人搞文字改革,黄侃指着钱玄同道:“二疯!我告诉你,你很可怜呀,现在先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读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大怒:“我就要弄注音字母,就要弄白话文,你管得着吗?”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后经老师章太炎一番劝解,双方才作罢。
黄侃对新学的拥护者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其中对新派风云人物胡适的奚落和责骂尤多。胡适任教北大,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黄侃高足傅斯年等人很快倒向新文学阵营。黄侃上课前,常常先骂一通胡适才正式讲学,一逮住机会,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聚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听到,心里很不痛快。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笑道:“且息怒,我在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在座众人哗然大笑。还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说完,他还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听此,无可奈何,一笑置之。
从感情上来说,黄侃依恋着传统文化。但骂归骂,他并没有像林纾等人那样,写出抨击胡适、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他深知,上课发发牢骚,骂骂人,是名士气,是潇洒;如果笔之于书,互相攻击,就是小家子气。他也知道,新文化代表着未来,曾对学生陆宗达说:“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绝不改变,但你一定要作白话文。”
进“章门”又入“刘门”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黄侃恰好和章太炎同住一栋楼。章太炎此时正在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国内改良派展开论战。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来不及上厕所,便从窗户朝外小解。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闻此异味,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是贵公子出身,且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考据训诂学大师,黄侃久闻其大名,敬仰其学问,便拜他为师。自此,黄侃跟随章太炎学习数年。
自视甚高的黄侃,常常目中无人,但唯独对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始终信奉太炎先生,有诽议其师的,他必定据理力争。章太炎也称他“性虽怪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写诗,经常请章太炎审阅。他对章太炎的字纸特别珍视,每获来信,就裱起来珍藏。章太炎知道黄侃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写几幅字、几首诗赠予他,黄侃每有所得便如获至宝。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却对一人以礼相待,这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在东京通过其师章太炎结识刘师培,二人甚是投缘。刘师培归国后组建“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一天,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聚会,胁迫众人拥戴袁世凯称帝,话才讲到一半,黄侃愤而起立,严词拒绝:“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即拂袖而去,到会人员也随之离开。
黄侃反对刘师培的政治倾向与帝制活动,与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一直秉持的民主革命思想有关。但他佩服刘师培治学功底深厚,尊重其学术成就。帝制活动失败后,刘师培声名狼藉、潦倒不堪,被兼容并包的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章太炎、刘师培、黄侃3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他的心思。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可当传人,黄侃即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结果第二天,黄侃用红纸封了10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欣然接受,此时已是1919年夏,离刘师培11月病重去世只有三四个月时间。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可见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
黄侃有一句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天赋异禀的他不幸于49岁就去世,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憾事。他身前虽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却被学界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提出古声十九纽说、古韵二十八部说、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等,得到广泛认可。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出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陆宗达、潘重规等著名学者,影响深远。
(执笔:张惠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