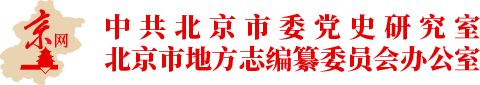《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东侧箭杆胡同20号(原9号)。整个院落分东西两部分,中间有门相通,总面积460平方米,建筑面积264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租住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编辑部随迁此处。陈独秀住东院,房主住西院。东院3间北房是陈独秀的住所和办公室,3间南房是《新青年》编辑部,两间东房供车夫和厨师居住。至1920年初离开北京,陈独秀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年时间。2001年,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胡同深处的这座僻静小院,我们仿佛看到陈独秀奋笔疾书、激扬文字的伟岸身影,仿佛感受到新文化干将们以笔当枪、披荆斩棘的昂扬斗志,仿佛聆听到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历史呼唤。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今貌
从宣传民主科学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高地
简居陋舍聚英贤,热血男儿问江山。100多年前,这里的一份《新青年》杂志和一群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大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铸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辉煌。
文学革命大剧在这里掀起高潮
《新青年》迁京前后,相继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从此,在《新青年》这块小小天地里,策划上演了“扫荡摧清”的一幕幕精彩活剧,引发新文化运动一个个高潮。
展现冲破旧文学束缚的昂扬姿态。陈独秀首举“文学革命军”大旗,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三大主义,以“甘冒全国学究之敌”的勇气,为这场文化斗争注入了革命的底色。在他的影响下,鲁迅从消沉中觉醒,相继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白话小说,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钱玄同从笃信古文的章太炎弟子一跃成为提倡国语、改革文字的新文化斗士,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胡适也由最初主张点滴改良,渐而成为倡导运用白话文的急先锋,并最早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同时,《新青年》还汇聚了刘半农、沈尹默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投身到文学革命的洪流之中。从《新青年》发端的这场文学革命,冲破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及其依附的封建藩篱,迅速蔓延全国。
引发新旧思想文化的激烈交锋。破旧立新的新文学与固陋保守的旧文学势同水火,《新青年》便成为新旧文化及其拥趸的战场。新派文学视旧派文学为死文学、假文学,主张“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不容他人之匡正”。钱玄同、刘半农合演了一出“双簧戏”。一个代表反对派,用假名致信《新青年》,指责其排斥孔子、废灭纲常,污蔑文学革命;一个代表《新青年》,针锋相对、指名道姓对信中观点和旧派人物展开批驳。旧派文学以林纾为代表,先是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公开回应,继而推出《荆生》《妖梦》两篇文言文小说,影射诋毁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极尽谩骂攻击之能事;最后发表向蔡元培辩难的书信,指斥新文学为“覆孔孟,铲伦常”的洪水猛兽。新旧两派的论争进入白热化。新派文学集中火力进行反击,阵地从《新青年》扩展到《每周评论》,特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栏,条陈旧派思想言论,进行集中揭露和批判。旧派文学与反动统治势力沆瀣一气,以解聘、封刊相要挟,对《新青年》及其同人进行打压,激起社会各界对新派知识分子的同情。陈独秀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集中宣示《新青年》同人的立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旧文化的激烈交锋,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扩大了文学革命的积极影响。
推动全国范围空前的思想解放。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全国,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等文学作品纷纷涌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座鲜明的界碑。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将白话文作为现代“国语”纳入官方教育体制,宣告了文学革命的胜利。文学革命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白话文的普及,带动中国社会从文学形式到思想认识,都开始打破封建禁锢,走向自由开化。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激进的态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体系,宣扬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理念;一批文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自觉拿起文学武器,向着封建礼教宣战,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实现了从文学革命向思想革命的转变,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一大批热血青年在《新青年》影响下,思想逐渐觉醒,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之中,各种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星罗棋布般争奇斗艳。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做了重要准备。
马克思主义真理在这里向全国传播
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推动着一些先进分子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重要契机。由此,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通过艰辛求索、比较鉴别,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涛巨浪。
十月革命胜利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窗口。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消息传来,为正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照亮了前路、带来了希望。《新青年》从介绍俄国革命入手,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高擎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在《新青年》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他鲜明地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是“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他向中国人民介绍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说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是“联合全世界的无产庶民……创造劳工的世界,求得人类的幸福”;他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认为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向着光明的未来进发,并满怀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同一时期,《劳动》《民国日报》《太平洋》等也对十月革命做了介绍。在李大钊引领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更多地将十月革命与中国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系统深入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五四爱国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新局面。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打破了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走俄国的道路被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为更多人所接受,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集中刊发8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3个组成部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顾兆熊《马克思学说》、刘秉麟《马克思传略》、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以及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解释社会问题。此外还刊载了陈溥贤、周作人《马克思的奋斗生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等译文。这期专号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理论领域的一次“隆重亮相”,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共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130多篇。在李大钊积极推动和《新青年》这面旗帜影响下,《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和《晨报》副刊等各地进步报刊群起响应,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文化书社、利群书社等各地进步团体遥相呼应,全国逐渐掀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潮流。
问题与主义之争夯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分化。《新青年》同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发生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胡适极力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针对具体问题一点一滴进行改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根本解决”的暴力革命论;李大钊鲜明地指出,既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并且只有借助主义这一“根本的解决”工具,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鉴别,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场论争还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可贵探索,并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向广大工人阶层,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新青年》杂志在这里迎来新生
《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办刊理念得以升华,思想内容发生嬗变。毫无疑问,地位独特、精英荟萃的北京,为《新青年》的新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开辟了广阔的舞台,成就了它办刊10年最辉煌的时期。实现从一人主编到同人办刊的转变。《新青年》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拉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办好《新青年》杂志,成为他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旧文化和旧社会的尝试。创刊之初,陈独秀一人主创主编,人脉不广、经费不多,稿源一半靠自己撰写,一半约自同乡好友,影响非常有限,曾因入不敷出面临停刊。迁京之后,陈独秀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之便,延揽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等一批志同道合者,《新青年》编辑作者队伍迅速扩大。尤其从第4卷第1号起,所有文章撰译组稿都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实行轮值编辑制度,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型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共同的目标和事业追求,使《新青年》同人结成一个新文化阵营,推动着新文化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新青年》由此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

陈独秀办公室复原图
实现从区域性影响到全国性影响的转变。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最初撰稿人主要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知名度和影响局限于上海、安徽等局部地区和陈独秀的同乡好友圈子,发行量徘徊在1000册左右。迁京之后,杂志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高等学校云集。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积极协助蔡元培,引进思想先进、用心改革文化教育和致力整顿社会风气的志士。他一方面邀请《新青年》初创时期的作者进入北大,一方面吸收北大革新力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使《新青年》与北大实现“一校一刊”的结合,成为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的著名刊物,发行范围遍及大江南北,甚至远及海外,发行数量长期保持1万余册,最多时近2万册。《新青年》编辑部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团结和凝聚了全国的革新力量,影响和培育了一代进步青年。《新青年》杂志被誉为“金针药石”“良师益友”“思想界的明星”,引领一大批“新青年”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来。
实现从宣传民主科学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陈独秀和《新青年》是伴随着时代脉搏跳跃的领舞者。《新青年》创办于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代背景之下。面对中国社会兵连祸接、资产阶级革命派彷徨迷惘的严峻现实,陈独秀认为,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从1915年创刊到1917年迁京前,其主旨在于思想启蒙、开启民智。这一时期,《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到风俗习惯和婚姻家庭,从人格修养、文化教育到思想评判和国民性改造,启蒙思想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目的在于全面“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917年《新青年》迁京后,世界局势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动,把一系列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摆在了新文化运动领导者面前,《新青年》逐步从致力于思想启蒙转变为关注“国命存亡”的时政。这一时期,启蒙文章逐渐减少,时政文章明显增加,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罪恶行径到反对军阀派系斗争,从唤醒民众运动到直陈社会改造问题,凸显了救亡图存的鲜明主题。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他们逐步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为阵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刊物之一。它吹响了民主与科学的战斗号角,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思想启蒙运动的熊熊火炬;它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指明了救国救民的前进方向;它承载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激励着人们乘风破浪、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