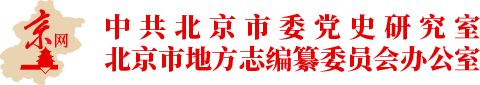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感慨:“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作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大红楼成为新思想、新潮流的聚集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摇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
执掌北大 整顿校风
蔡元培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26岁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仕途前景光明。32岁时,因对清廷变革绝望,毅然弃职返乡。此后几年,他辗转绍兴、上海、青岛等地,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还曾创办《警钟日报》批判日、俄占领东三省的罪行,组织建立光复会,并亲自参与研制毒药和炸弹,试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
1906年,蔡元培到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讲授国文和西洋史。次年,他辞去教职,赴欧洲留学,学习西方文化及教育。辛亥革命爆发时,蔡元培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受孙中山邀请,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南北统一后,继续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着手改革封建教育体制,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尝试建立起我国近代教育体制,并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因对袁世凯的擅权和专制不满,半年后,他退出内阁,辞去教育总长职务。1912年9月,再度赴欧留学。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动。9月,身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电报,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回国时,针对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蔡元培给自己定了“三不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回国后,有朋友劝他别去就职,因为北大太腐败,如不大加整顿,反而弄坏了自己的名声。也有朋友说:既然你知道它,就更应该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是尽了心。尽管北京大学校长是由政府任命的,但在蔡元培心里,他是去办教育,不是去做官。于是,他抱着“切实从教育着手,使吾国转危为安”的宗旨,毅然前往就职。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设之初主体为仕学院,所收学生多是在京官吏。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大学,并进行初步改革,但因官僚积习很深,改革很不彻底,校政极为腐败。不少学生官气十足、无心学习,他们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靠拉拢应酬混日子。教员敷衍塞责,平时不用功,上课照本宣科,学生提不起兴趣,只能打瞌睡、看杂书,学风很差。学生在乎的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毕业后的出路。专门研究学问的老师不一定受欢迎,在政府做官的兼职教员却颇受追捧,因为学生想要毕业后通过老师谋取官职。
蔡元培曾在北大任过教员,深知这种腐化的学风、校风,根源在于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学生的求学观念出了问题。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大学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为求学而来。
上任伊始,蔡元培大力整顿校风,尤其注重对师生的品德修养和纪律约束。当时的学校章程规定:各科选择品行敦笃、学问优长的学生评为优待生,优待生可以免交一年学费;班长或舍长在一学年内能够恪守校规,成为同学之表率的,可给予一定奖励;对于品行不修、学业荒废的学生,则受到谴责,严重者甚至可以令其退学;有对职员无礼、行为不检点的学生,进行严肃教育,令其悔改;对损害学校名誉的学生予以处理。同时,解聘了一批学术水平低下、态度不认真和品行不端正的教员。
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唤起其对自身人格的重视,在蔡元培提倡下,进德会、新闻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进德会、新闻学研究会、学术讲演会等由他亲自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蔡元培特意婉请个别行为不检点的教员入会,帮助其改造德行。校内还经常举办演讲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逐渐盛行,师生都活跃起来。同时,创办了许多新颖独特的刊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教授创办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故》月刊等,学生创办的有《新潮》《国民》等。新旧思想文化在一波波论争、交锋的热潮中刷新着学生的思想观念。
蔡元培希望人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推行社会教育。1918年,北大开办校役夜班,230余位工友参加。夜班教师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许多学生热心施教,除认真授课外,还发起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学生们逐渐懂得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强化了积极服务社会的意识,教员、学生和校工们无形中更加趋于团结。
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学生们逐渐懂得: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研究学术不是为做官,也不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此后,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认真研究学问、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追求进步与革新的种子在学生心中萌芽。短短两三年间,北大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变成为全国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北大走上历史舞台。
抱定宗旨 改革体制
蔡元培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管理体制,首先从改革学校领导体制开始。他反对校长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民主办校。按照教授治校原则,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创立各种会议制度,凡事让大家尽量发表意见,充分施展才能抱负。他作风民主,对各方面人才,一经认定就完全信任,放手让其工作,不过多干涉,使人尽其才,各显其能。
原来的北京大学校园仿佛一座衙门,学生有事请示校长时须写呈文。蔡元培非常厌恶这种做法,上任后立即发出布告,废除学生写呈文向校长请示的规定,他的办公室不设保卫和服务人员,师生有事随时可以找校长沟通,逐渐养成全校人人平等的氛围。他还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作为师生交流平台。《北京大学日刊》除发表校内消息外,还刊发师生论文,营造研讨学问的氛围。蔡元培还把学生的意见建议送校刊选登,并选择可行性建议付诸实行。
学科设置也是蔡元培的改革重点之一。此前,因学法科为做官之捷径,考法科的学生很多,考文科的较少,考理科的尤其稀缺,造成重法科、轻文理的不平衡现象。蔡元培主张“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强调基础理论重于应用科学,并大刀阔斧地改革学科设置。他从教育发展及国家需要大局出发,通盘考虑,扩充文、理科,调整法科,取消工、商科,正式设立学系,创办研究所,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的偏向。同时,加强大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育,为形成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打下坚实基础。
推行平民教育,打开校门,开放女禁,是蔡元培开风气之先的改革举措。原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多为官宦子弟,寒门子弟较少。蔡元培改革招生制度,不看资格、出身,只注重学识、成绩。从1917年暑假起,连续3次招生,凡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报考,严格以成绩优劣为标准,择优录取,使贫寒、有志青年能进北大学习。出身贫苦,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先生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
北大还招收旁听生,只要有相关学力,经相关学科教员面试认可后,即可入校旁听。方便之门一开,各地前来旁听的青年络绎不绝。有些没办旁听手续的青年,也“溜”进来“偷”听,他们和正式学生一样可以领讲义,自由进出图书馆,不受歧视。这些旁听生住在校外价格便宜的公寓里,到北大旁听,苦读上进,不少成为栋梁之材。有些旁听生在北大受到新思想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也曾在北大旁听过课。
1919年春,求知若渴的甘肃女学生邓春兰给蔡元培写信,表示想到北大学习。此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不在北大,没能及时处理。6月,邓春兰发表公开信,呼吁大学开女禁。8月,《少年中国》刊出妇女问题专号,转载此信,一时引起很大反响。蔡元培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教育部规程没有规定不准收女学生,明年招生时,学力条件符合要求的女学生,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只要考试通过,就可录取。
不久,北大便有了第一位女学生王兰。王兰是江苏人,因病失学在家,想进北大求学。其弟王昆仑当时在北大就读,去问蔡校长是否可行。蔡元培问她敢来吗?王昆仑回答她敢!蔡元培说可以让她来试试。就这样,王兰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她到校时,因错过春季入学考试,学校准许其先入校旁听。此门一开,其他女学生也纷纷前来求学。1920年春,包括王兰、邓春兰在内,共有9名女学生到北大旁听,这年暑期经入学考试合格后,都转为正式学生。
男女不同校的惯例一经打破,影响很快波及全国,很多学校效仿北大的做法,开始招收女学生。
顺应潮流 融化新知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他接手时的北京大学是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尽管旧教员中沈尹默、钱玄同等已开启革新端倪,但因受政治派别、教育体制、人事关系等因素牵制,北大革新步履维艰,封建守旧思想充斥各个学科。尤其在文科教员中,守旧派占据上风,特别是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成为革新障碍。当时,旧派的文科学长已辞职,这一职位由谁接任成为广大师生关注的焦点。
蔡元培抓住这次机会,从整顿文科入手,不拘一格,广纳贤才。他入职北大不久,就聘请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正在北京办事,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为请陈独秀,蔡元培差不多每天登门拜访,有时去得很早,主人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坐在房门口的凳子上耐心等候。陈独秀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辞,他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蔡元培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态度打动了陈独秀,经过多次深入交谈,陈独秀慨然应允。陈独秀到北大后,协助蔡元培对北大人事管理、领导体制、学科建制、招考制度等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卓有成效,使北大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们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发起文学革命,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陈独秀是新文化阵营中影响最大、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他平时不注重细节,说话不讲方式,得罪了一些人,不少人怕他,甚至讨厌他。蔡元培却对他极为器重和爱护,对其弱点也不求全责备。梁漱溟曾评价:陈独秀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如果得不到蔡先生器重、爱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更无用武之地。一次,北大三院教授会上发生争执,陈独秀当面直通通地指责理科学长夏元瑮,一些教授对陈独秀的盛气凌人不满,形成僵局。蔡元培出面劝解,才为他解了围。
1918年年初,蔡元培邀请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全力支持李大钊整顿图书馆。在办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批准李大钊从国外购进大量图书,包括许多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和一批社会主义文献,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辟出一片沃土。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成为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北大图书馆成了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在此聚会,向李大钊请教问题,交流研讨进步思想。毛泽东就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
同年7月,胡适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经陈独秀举荐,蔡元培看到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十分欣赏,便请他到北大任教。1918年,刘半农、周作人等陆续被邀请到校任教。之后,鲁迅也到北大兼课。这些新聘教授,加上原来在北大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形成强大的新文化阵营,学校气象为之一新。
蔡元培聘请教授不拘一格,不受派别约束,每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言之成理,就让其并存,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以文科为例:史学方面,有信古派陈汉章等,有疑古派钱玄同、胡适等;文学方面,有文言派黄侃、刘师培等,有改良派朱希祖等,也有白话派胡适、陈独秀等。教授们对同一事物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一时间,北大课堂成为各派学说竞争辩论的场所。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并非无所选择,例如:他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前提是不提倡复辟。这种兼容并包而有所提倡的态度,使北大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孕育地。
北洋军阀政府和守旧派视北大为异端和洪水猛兽,视蔡元培为始作俑者,纷起攻击。1919年3月,段祺瑞派的《公言报》刊登《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斥责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实亦太过”。守旧派代表林纾写公开信、小说,攻击北大和蔡元培。不断传出政府将要干涉北大的消息,甚至传言要在景山架炮轰击北大。在此情况下,有人登门劝说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之。蔡元培回答:“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倾力奔走 营救学子
在蔡元培倡导下,北大学生逐步确立研究学术为求真理的理念。为避免学生陷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另一个极端,蔡元培提出“读书不忘救国”的理念,将学术思想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使学生能从安静的课堂里,寻找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在这种理念影响下,学生们逐步认识到:身处国家危急时刻,只有为救国而读书,才是正确的选择。
学生们怀着爱国热情,关心时事发展,密切关注中国外交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期待公理战胜强权,要求取消各国在华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交涉,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最为关注的敏感问题。4月30日,和会不仅拒绝讨论中国的合理诉求,还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字承认。
5月2日,蔡元培召集学生代表和班长开会,讲述巴黎和会列强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之后,他把北洋军阀政府密电签字的消息告知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5月4日,北京高校3000多名学生结队游行请愿,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32名学生被捕。这天夜里,北大学生聚集在第三院大礼堂,商讨营救同学的办法及处理善后事宜。学生们相顾无言,束手无策,沉浸在肃静无声的气氛中。忽然,大家听到有急切的脚步声走来,竟是蔡元培校长。看到校长,学生们害怕受到训斥,有的大声呼叫,有的放声大哭。
蔡元培走到前台,温和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他继续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日起照常上课。”蔡元培还找来修订法律馆总裁王宠惠,请其帮忙研讨与警察厅交涉的法律手续问题。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实权掌握在段祺瑞手里。蔡元培连夜拜访受段祺瑞倚重的孙宝琦,请他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孙宝琦因担心事情闹得太大,表示犹豫。蔡元培就坐在会客厅等待,从晚上9点左右,一直到午夜12点还不走。孙宝琦无奈,劝他先回家休息,答应明天去试一试。5月5日,蔡元培和各大专校长开会议定:学生此举是集体公共行动,不应由被捕的少数学生负责,应当由各校校长负责待罪。51岁的蔡元培日夜奔走,有人劝他量力而行,恐危及自身,他笑着说:“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几天后,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出于多方考虑,呈请辞职。经各方面大力挽留,于9月20日返回北大。
蔡元培认为,学有所成才能更好地爱国、救国。五四运动以后,他看到学生们有偏于政治活动的倾向,而忘却学生以读书为主业的本职,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使青年们有所觉醒。他帮助不少学生出国求学,寻求救国之道,同时还指导学生力所能及地为社会服务。在他影响支持下,北京大学的校工夜班、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很快发展起来,学生们走出校门,为劳苦大众服务。
此后几年,政治环境复杂多变,蔡元培多次请辞北大校长,未获批准。1923年春,他因不满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政策离职南下,后转赴欧洲考察,从事著述活动。他离校后,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这一时期,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教授会及各种委员会,制度科学完善,运转民主高效,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北大不因校长之去留,影响校务之正常运行。1927年,蔡元培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之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40年病逝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