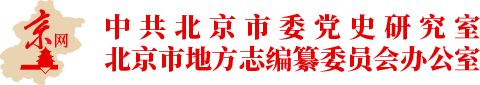1949年,国民党政府将大批人员和物资转移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却有一位院士拒绝迁台,公开跟自己的学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唱反调,还把麾下社会学研究所整套人马、辎重留在南京,交给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他就是首倡社会调查实证学风的社会学家陶孟和。

陶孟和
首倡社会调查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1887年生于天津,早年在近代教育家严修创办的家塾中上学,半天读四书五经,半天学英文和数理化知识。1906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4年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习社会学。其间,与同学梁宇皋编写的《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将社会调查方法与中国社会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1913年,陶孟和获得博士学位,抱着“调查入手,改革社会”的宏愿,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翌年,他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开设政治学、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根据讲义出版的《社会与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开创性著作。他善于运用西方学科知识,评论中国社会问题,所授课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理论成果,受到学界高度认可。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京。作为“新派教授”,陶孟和用实际行动给予支持,积极为杂志撰稿,以昂扬的姿态投身思想启蒙与知识传播。1917年1月,他的《人类文化之起源》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同期发表的还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后,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轮流编辑杂志,并发表10余篇文章,如《社会》《新青年之新道德》《生存竞争与互助》等,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深刻道理,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就读于北大,后成为历史学家的金毓黻曾回忆:陶孟和参与编辑《新青年》,使其“北大社会学教授”的名声得到学界和世人的认同。
1918年春,陶孟和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首设《社会调查》专栏,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实证学风,“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调查既能了解中国社会的长处,又能找到社会的弊病,从而找到改革社会的方法。其中,“乡村调查最为重要”,中国以农业为本,绝大多数人务农,社会调查应从乡村农民生活着手。专栏还刊登了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农民境况的报告。在他的倡导下,《新青年》陆续发表了一些社会调查报告。
从底层民众生活中寻找改革社会的答案,是陶孟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显著特点。进北大不久,他便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青年们走街串巷,调查北京内外城各区302名人力车夫的职业与生活情况。人力车夫大多20~40岁,每天工作约10小时,“终日暴露于风雨寒暑之中,汗透衣服而不能脱,其生活之痛苦,已极可惨”,收入却非常微薄。他们每天收入51~80枚铜元,除去赁车费约剩一半,当时每人每天生活费需15~20铜元,劳作一天仅能糊口。因收入太低,加上北京本地人尤其是旗人“尚奢侈”,不像山东人等外乡来者“俭省”,很少有人能存下钱,更不用说让子女受教育了。
调查中,陶孟和询问车夫,此前从事什么职业?得知绝大多数是小商人、手艺人,其他为无业者、农民,因生活所困,只得出卖苦力。挣到的钱怎么“消遣”?有的喜爱听戏、听书,有的“流于怠惰”,沉溺于赌博和嫖娼,这对“社会道德”和“社会卫生”,“皆有极恶之影响”。他指出,这是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应为车夫改善环境,建立“俱乐部一类之游戏场所”,然后“实施教育之计划”,使其成为“掌握技巧的工人”,“提高人力车夫即是提高社会”。
此后,陶孟和还发表《中国目下的失业问题》《中国劳工生活程度》《贫穷与人口问题》《新贫民》《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等关注民众生活、分析社会问题的文章,体现出他难能可贵的底层关怀和独到见解。
考察战后欧洲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跻身战胜国行列。为庆祝这难得的胜利,北大在天安门前举行讲演大会,陶孟和与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发表了演讲。陶孟和发表题为“欧战以后的政治”的演说,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抱着无穷的希望”,期待借助这次历史契机,推动国内社会变革,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
1919年3月,全国高等以上专门学校及各省教育会推举陶孟和、郭秉文等人,赴欧洲和日本考察各国教育。陶孟和在考察第一站伦敦时,遇到了李四光和丁燮林,慧眼识才的他立即向蔡元培推荐两人,并致信胡适,盛赞他们是“不多觏之材”,促成两人归国后到北大任教,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
此时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刚刚经历外交重挫: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之时,正是陶孟和一行到达巴黎之际,这真是“劈头就遇着一个大棒击”!尽管内心极度失望,巴黎和会会场又近在咫尺,但他没有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依照原计划继续欧洲考察行程,广泛深入调研,着重分析巴黎与欧洲形势,并对战后欧美国家及社会现状进行冷静分析,从而理性思考民族命运。
考察期间,陶孟和还不忘为北大图书馆精心选购英文书籍,并向当地华人、留学生推介《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他还以“明生”为笔名,在《每周评论》开设《欧游记者特别通讯》专栏,连载考察期间的见闻与思考,直至1919年8月该刊被迫停刊。
同年12月,陶孟和将考察欧洲的情况写成《游欧之感想》,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文章指出,巴黎和会并未改变强权跋扈、弱肉强食的世界。他告诫读者,重要的不是谴责列强出卖中国利益,而是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欧洲早已自顾不暇,就算有心也没有能力照顾中国的利益。“我们弱小的民族,自己不努力,反向他们去诉冤,求他们的帮助。”这原本就是缘木求鱼,何其天真!事实上,这时的欧洲仍是战时政府,正是这帮“旧人物”主导巴黎和会,“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地图上的颜色改变改变,把德意志逐出强权之列,换了一个东方崛起的日本”。他断定,德意志的战败将导致欧洲力量失衡,为日后更大的灾难种下祸根。果不其然!十几年后,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陶孟和对欧洲局势的判断极富远见,体现了一位社会学家的深邃眼光。
倡导“好人政府”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逐渐分化成革命和改良两大阵营。因为政治理念不同,新文化运动阵营开始分化。陶孟和与胡适同为英美留学生,两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1920年夏,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移至上海,引起陶、胡等人不满。这年年底,陈独秀去了广东,把《新青年》交给陈望道负责。陶孟和为此主张“停刊了事”,陈独秀便在给《新青年》同人作者的回信中反问:“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此后,胡适还给《新青年》写过几篇文章,陶孟和却再未投稿。
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7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称本不想谈政治,但现实的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妨害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奋起抗争。两年后,他又与胡适、蔡元培、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参与倡导“好人政府”。
这时的陶孟和,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中国的政治仍是专制的,社会必须改革。尽管他关心民众生活,并为此奔走呼号,但他没有像李大钊、陈独秀那样选择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而是作为一位知识精英,发挥自身专业学识,为社会改革不懈努力。
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改组内阁,出任国务总理,罗文干、汤尔和分任财政总长、教育总长,这届内阁因此被称为“好人政府”。尽管陶孟和等人全力支持,提出一系列治国方略,可是,这个先天畸形的“好人政府”,不过是吴佩孚借以结好孙中山、打击皖系奉系军阀的空架子,仅仅存在72天便宣告破产。“好人政府”这个民主共和幻梦的破灭,让陶孟和反躬自问,这种“少数人的责任”——将广大人民排斥在外的知识精英救国方案,怎么可能成功呢?!
由于这次失败,陶孟和开始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世上的事业没有捷路可走”,应“设法造有资格的人民”。1923年9月,他在《中国的人民的分析》中提出:中国99%都是小农人,他们跟商人、工人、有资本的工业家、知识分子群体一样,都没有资格维持共和政体。“现在不要空谈制度,先去设法造有资格的人民罢。”
此后,陶孟和成为《现代评论》主要作者之一,笔触所及,涵盖教育改革、土地人口、国际评论等广泛领域。1926年,他创办北平社会调查所,后与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长期担任所长。抗战时期,他坚守社会学研究所这座孤岛,培养了严中平、梁方仲、千家驹等青年学者,完成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陶孟和发文反对,思想进一步左转。1949年,他留在大陆,还动员旧日同事共赴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研究所所长,1960年因病去世。
(执笔:贾变变 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