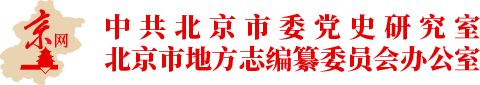1919年5月3日深夜,一位北大青年学子奋笔疾书写下:“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是为“五四宣言”文言版中的一段话。起草宣言的这位青年学子,也是五四运动发起者、筹划者之一,更是走在五四游行队伍前列的学生领袖,他就是许德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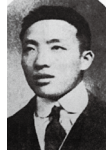
许德珩
创办《国民》杂志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沈家冲,自幼受到父亲的民主革命思想熏陶,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他考取北京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国文系。许德珩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件夹衣过冬,为节省灯油和御寒取暖,大多数时间他会待在图书馆或教室里看书。校长蔡元培曾称赞他“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积久不懈”。
1918年的一天,许德珩正在图书馆,看到一群学生围着一个人热烈地谈论着。此人身材魁梧,留着浓密的八字胡,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面带微笑、态度诚朴谦和。当得知这就是仰慕已久的李大钊时,他便马上加入到讨论中。许德珩很早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尤其从《国情》《厌世心与自觉心》和《青春》等文章中,感受到强烈的战斗精神,并深受影响。
许德珩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盛铎,是著名藏书家,他通过许德珩,把自己一部分藏书送给了北大图书馆。此后,许德珩和李大钊更加熟悉了,二人常在李大钊办公室,畅谈新思想以及国家前途命运等问题。虽然许德珩是学生,但只比李大钊小一岁,二人之间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中国人民坚决反对。21日,北京各大学及少数天津学生代表2000余人,向总统府请愿,反对协议的签订,许德珩是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之一。这次请愿活动虽未达到目的,却使他明白团结、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7月,许德珩与邓中夏等人创建以“救国第一”为宗旨的学生救国会,并筹备创办《国民》杂志,邀请李大钊做指导。国民杂志社于10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各地、各校80多位社员到会。蔡元培、邵飘萍等也很支持,作为来宾参会。许德珩主持会议,报告筹备经过并说明创办杂志的必要性,会后发表国民杂志社成立启事。
不久,《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olshevism的胜利》,第一次系统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李大钊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许德珩感到震撼,视之为“卓越”之作,反复研读,心潮澎湃,认定俄国十月革命才是自己所期许的真正革命。
1919年1月1日,《国民》杂志创刊。蔡元培作序,对杂志寄予厚望,愿其永葆唤醒国民之初心。许德珩撰写《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的发刊词,阐述“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的办刊宗旨。《国民》杂志具有十分鲜明的反帝爱国色彩。许德珩既是这个刊物的负责人又是作者,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他在杂志第1至4期发表《外交与民气》《人道与和平》等10篇通论、专论和评论文章。他还邀请李大钊撰写《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揭穿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并吞中国的隐语”。杂志第5期发表北大学生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较早译本之一。
《国民》杂志会聚了一批爱国青年,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编辑部大多数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许德珩的贡献尤为突出。
奋笔起草五四宣言
1919年5月2日,许德珩从校长蔡元培处得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将转交给日本。他们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里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次日在北大举行学生集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及其他十几所学校代表共计1000余人,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推举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任大会主席,黄日葵、孟寿椿负责记录,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会上,许德珩、易克嶷等许多学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罪行,令大家悲愤欲绝。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手指,写下“还我青岛”4个大字,全场为之动容。刘仁静为激发大家的斗志,拔刀准备当场自杀,以死警醒世人。会场上响起“游行去”“去总统府”“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气氛苍凉悲壮。
集会得到蔡元培的默许,他安排庶务科给许德珩一刀纸,起草宣言。当晚,许德珩奋笔疾书,写下文言文版《北京学生界宣言》: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宣言写好后,许德珩又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当时已近深夜,因弄不到白布做旗子,他扯下自己仅有的一条白床单。在微弱的烛光下,许德珩把床单撕成条状,用墨笔写下标语和口号,一直忙到天亮。其他同学也都在为准备示威游行的事而忙碌,有的找竹子做旗杆,有的写标语,彻夜未眠地赶做出了几百面大大小小的旗子。
五四被捕入狱
5月4日下午,天安门前,北京各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闻讯,先是让教育部一个次长来劝说学生解散,之后又命步军统领李长泰带着军警来阻止学生游行。李长泰从汽车中钻出,声嘶力竭向学生喊话,要求马上解散,甚至要用武力驱散学生。学生们义愤填膺,怒不可遏,齐声高呼“打倒卖国贼”,准备和军警搏斗。李长泰见势不妙,不敢继续弹压,最后只得声言学生举动要文明,便灰溜溜地走了。
集会中,学生们宣读并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即充满爱国激情的“五四宣言”。
“五四宣言”是许德珩五四前夜紧急起草的,又因种种条件所限,在五四当日集会和游行时并没有印出来,多日后才被新闻界报道,此后便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
在五四游行中,许德珩自始至终走在队伍前列。他与其他同学不顾北洋军阀政府军警的威胁和干涉,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前进,欲前往日本等国使馆抗议。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阻止,他们向美国大使馆递交陈词后,从东交民巷经东长安街,穿过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处。
沿途,许德珩与学生们散发传单,许多民众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赵家楼胡同曹宅大门紧闭,学生们纷纷将标语、旗子投掷院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砸开围墙上的窗洞,设法跳进院内,打开大门,许德珩与游行学生一起,像潮水般涌进。学生激愤之下,一把火烧了曹宅。随后大批军警赶到,在现场和沿街抓捕未来得及散去的学生。许德珩与抓他的军警扭在一起,双方僵持不下,滚翻在地,最终被军警捆了起来,与北大同学及其他学校学生被捕。
狱中赋诗言志
许德珩等被捕学生受到军警的公开羞辱。军警指着他和易克嶷说,“就是这两个家伙在煽动”,并故意把他们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对被捕学生进行讯问,许德珩据理力争:“我等先在街上游行,然后到公使馆求见美公使主持公理,因公使未见,我等又往东城曹汝霖家……我等找曹汝霖本欲向他辱骂,并无放火意思。曹汝霖对于中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忿气发生。”
他们被关押在一个极其拥挤肮脏的小监房,里面只有一个大通铺,东西两边各放着一个尿桶,臭气熏天。每半小时还要听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是活的。到中午才能“放风”,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每人每天只给一个窝头,就着白水充饥。
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许德珩以诗言志: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由于各校、各界的积极呼吁、营救,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
随着运动进一步发展,5月底,受北京学联委派,许德珩与黄日葵等南下,联络发动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五四运动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爱国运动。6月28日,在全国人民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
1920年年初,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回国。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担任九三学社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成为著名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1979年,近90岁高龄的他,经邓颖超和乌兰夫介绍、中共中央批准,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执笔:王灵)